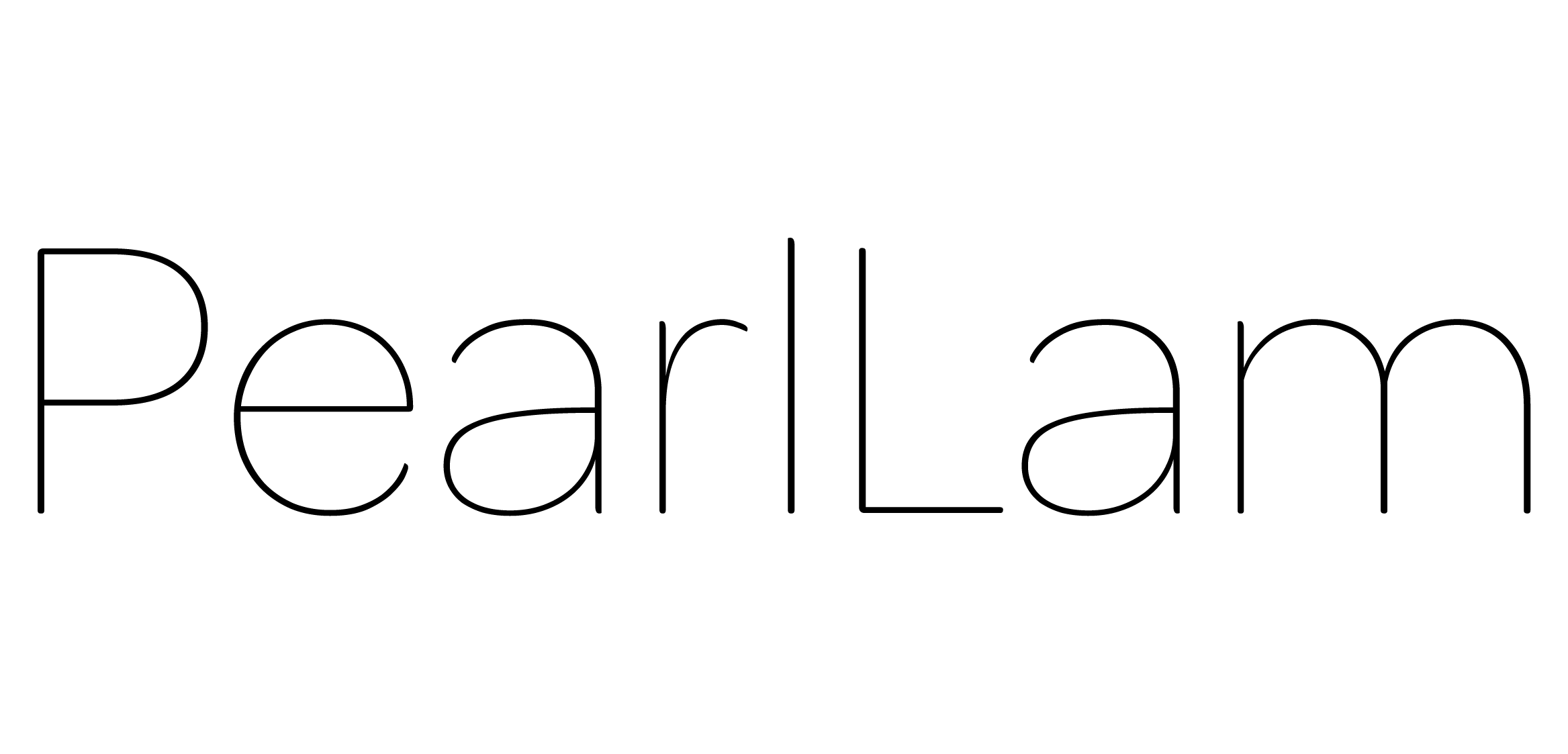馬可魯與策展人陳浩陽對談在香港藝術門的最新展覽,以下是對話的節錄:
D:您當年是如何加入「無名畫會」?
M:關於這個問題,其實我已被問及很多次,我希望闡明一下。「無名畫會」是為了1979年舉辦的第一場公眾展而成立的。因為我們要舉辦展覽,官方要求我們想一個團體名稱。我們思索再三,最終取了「無名」這個名字——我們認為「無名」可能更好。我們從70年代初就開始聚會了,當時我們每天的聯繫並不緊密,就是一個朋友圈子,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目標,不同的風格……後來因為我們在一起工作,逐漸地開始交流思想以及我們對社會和藝術的觀點,關係便越來越密切,尤其是因為我們這些藝術家都出生在30-50年代,同樣面對我們不喜歡也不能接受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的官方藝術。所以,我們開始自學藝術。從1972年到1973年,我和那些藝術家有過接觸,而「無名畫會」中有幾位比較年長,大約比我大7、8至10歲,但也有的藝術家比我小3至4歲,所以我在畫會中年紀居中。1975年,我們曾在張偉的家中舉辦過一場地下展覽。
D:張偉的家。
M:當時大約有11位藝術家。在1979年的第一次公眾展上,我們大約有20至30個藝術家參展。「無名畫會」活躍於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後舉辦了兩次展覽。後來,我們在80年代中期解散,畫會中的一些人離開中國出去進修,有的去了美國或其它地方。
D:「無名畫會」的原名曾是「玉淵潭畫派」嗎?「玉淵潭」與「無名」有什麼關係呢?
M:「玉淵潭畫派」是圈外人在70年代初期到中期給我們這個小藝術團體起的名字,因為當年我們經常去幾個地方畫畫,在大多情況下,我們去的地方離現在的北京不太遠,甚至可以說是更近,因為北京越來越大了。當時的湖、河、山等一切自然景色現在都成了人造公園,但那時的郊野很漂亮,十分適合我們畫畫,就像玉淵潭和香山,有時我們亦會去故宮。由於當時的交通不便,玉淵潭是我們70年代最常去的地方,所以圈外人便稱呼我們為「玉淵潭畫派」。實際上,這並不是正式的團體名稱,只是圈外人對我們的稱呼。
D:那段時間到戶外畫畫是否常見?
M:如果多人聚集一起做事,可能就會比較麻煩。基本上,如果您只是畫風景是沒有問題的。但我們不准去城外有些地方,不准拍照,更不用說畫畫了,人們會想知道您在那裡做什麼。
D:毫無疑問,「無名畫會」是一個沒有遵循70年代主流的社會現實主義風格的草根團體。這個團體的核心信念和願景是什麼呢?
M:我認為我們的信念和願景十分明確,我清楚記得在中國的那些年,我們真的不喜歡遵守那些藝術規則。雖然當年有很多全國性的藝術展覽,但完全超出了我們對藝術的看法。當年我們一起工作,儘管主要是創作小尺幅的風景畫,但我們仍然廣泛閱讀、並針對藝術展開了很多批判性討論。
D:當時主要是創作紙本作品吧?
M:我們的創作方式非常輕便,所有的畫都反映了我們的藝術觀點。多年來,我們試圖通過描繪自然來闡明藝術語言。如今,我們稱之為“為藝術而藝術”。我們不同意當年將藝術視為其它事物的工具的做法,所以我們試圖尋找什麼是藝術,然後只畫風景。對我們來說,尋找藝術完整性是一段漫長的旅程,我們希望理解自然以及傳統藝術觀點的含意。
D:因為您們去同一個地方一起畫畫,所以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的主題,亦因此為整個團體提供了一個共同討論的參考。
M:當時下班後,我們就自覺地去到現場並肩作畫。雖然是一樣的風景,但我們每個人迥異的性格卻令各自的畫面呈現出不同的風景。我們會選擇各自需要的東西,如:色調、氛圍、感覺、光線、顏色。有時我們會構思主題,但有時我們沒有限制,畫作很自然就畫出來了。
D:您有否留下任何檔案或文字記錄您們的討論?
M:70年代間,我們沒有考慮過記錄。直至1979年,我們舉辦了第一次展覽,才開始有一些參考資料。在70年代,如果您想記錄可以選擇寫日記,我當年亦有寫下來,但多年後已遺失。我們當年沒有相機,也沒有意識到我們在創造歷史,所以很難從這些討論中找到任何記錄。
D:當您現在回看1970年代的畫作,您會有哪些回憶?看到這些早期的作品時,您現在會想什麼?
M:1979年後,我們這個團體越來越分離,每人朝著自己的方向前進。對我來說,從1976年開始,我們就一直在一起,畫風都越來越接近,但我則越來越厭倦。所以,我找到了自己獨有的方式。當我回顧我所有的早期作品,我並不真正關心畫畫技術。那些年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我學到了很多,特別是學會了理解自然,自然呈現在我的畫作中,我練習了現代繪畫的基本技巧:顏色、光線、色調、筆的重量,還有控制。我在1970年代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大自然中完成,其中只有少數是憑記憶畫的,大多數畫作從頭到尾都是在大自然中完成,回到家裡我一筆未改,所以我認為當年藝術的實踐更為重要。直到現在,儘管從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代到我的近作會有很多變化,我仍會質疑什麼是藝術?我的藝術原則是什麼?
D:自然是一個起點。在過去的50年間,您是如何將重心從畫什麼轉移到如何畫畫呢?您所指的如何繪畫是什麼意思?
M:有一個詞對我來說很重要,我糾結了整整50年,到現在仍然是很重要——就是“重點”。70年代,當我日復一日地在戶外作畫,試圖捕捉最重要的元素,將自然轉化為繪畫時,我不得不考慮色調和組合,筆觸面對自然時何時結束,何時停止。而我們的藝術只來自大自然,不是從博物館中學習歷史。還記得70-80年代,我們討論過很多關於中國水墨畫的話題,尤其是宋、元朝代等早期的大師,甚至是近百年的黃賓虹這類的畫家。我可以將他們與保羅·塞尚 (Paul Cézanne)、文森特·梵古 (Vincent van Gogh)或卡米耶·畢沙羅 (Camille Pissarro)進行比較,並找出這些藝術家中的重要元素。我發現他們幾乎同等重要,並在他們的畫作中取得了相似的結果。他們對繪畫的理解都非常高。在1980年代後期,我開始創作抽象畫,在紐約時選讀了一些書,發現自己有一些很喜歡的藝術家,如賈斯珀·瓊斯 (Jasper Johns)、威廉·德庫寧 (Willem de Kooning)和阿道夫·萊因哈特 (Ad Reinhardt)。馬克·羅斯科 (Mark Rothko)的作品讓我對他作品中的人類狀況和靈性產生了非常強烈的感覺。我喜歡的藝術家哲學來自阿道夫·萊因哈特(Ad Reinhardt)。他出版了一本名為《藝術即藝術》的書。我買了後讀了很多遍,它總是讓我想起19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所研究的黃公望,趙孟頫和黃賓虹,我總是將他們做比較,因為阿道夫·萊因哈特(Ad Reinhardt)經常問“什麼是藝術?”,但他從不回答什麼是藝術,他開始尋找什麼是藝術。70年代的黃賓虹也是如此。如果您在做藝術,您必須先明白什麼是禁忌。如果您瞭解這些禁忌,那就更能理解什麼是好的藝術。
D:藝術是禁忌?
M:禁忌是您不應該做的事情。古代中國有一個邏輯問題「白馬非馬也」。白馬不是馬,白馬就是白馬,馬就是馬,馬不是白馬。這是一場邏輯詭辯,和我讀“藝術即藝術”時的情況非常相似。他通過瞭解什麼不是藝術來尋找什麼是藝術。
D:只有通過非藝術,人們才能理解藝術可以是什麼。
M:我早期的作品和著作都談到這一點。從我的《八大系列》到現在的作品,我不希望除了藝術本身,我的藝術被移作他用,即使我知道這種想法是保守的,不像當代藝術,是現代主義,但這是我的想法……
D:藝術是一種自由的表達方式。藝術家不應限制自己去定義什麼是藝術。藝術可以是它想成為的任何東西。我很高您提到阿道夫·萊因哈特(Ad Reinhardt),這有助觀眾更理解您的想法。您在北京的時候已知道馬克·羅斯科 (Mark Rothko),還是搬到紐約才知道的?
M:實際上直到90年代初,我才真正開始留意馬克·羅斯科 (Mark Rothko)和阿道夫·萊因哈特(Ad Reinhardt)。在去紐約之前,我已經很喜歡賈斯珀·瓊斯 (Jasper Johns)。直到 90 年代初,我受到了阿道夫·萊因哈特(Ad Reinhardt)提出的理論和觀點的影響。
D:我以為您先去歐洲,然後從歐洲搬到美國。
M:1988年1月,我去了歐洲柏林; 同年11月,我到了紐約。所以我曾在德國、瑞典和丹麥逗留。
D:您是1988年11月到的紐約,是嗎?80年代已經有不少藝術家移居紐約,對於很多來自中國的藝術家來說,自然的反應就是反思自己的身份,很多人都把它作為畫作主題當您搬到紐約的時候,通過作品來反思身份對您來說很重要嗎?
M:我認為這是大多數中國藝術家常見的題材,他們有那樣的經歷。對我來說也是,但那是很久以後的事。在去紐約之前,我去了歐洲旅行。無論我去哪裡,我都會去博物館和畫廊,如柏林、斯圖加特、科隆、瑞典和丹麥。當我來到紐約時,我讀過一些關於紐約的東西,並且已經對一些現代主義者非常熟悉。所以,對我來說,去紐約的緩慢旅程不像一些人直接從中國飛到紐約。對我來說,我非常想家。應該叫文化思鄉。這種感覺出現在1993-94年左右,我開始創作《八大系列》。